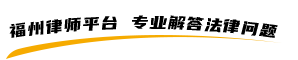蔡律師前文討論了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二)第5條(以下簡稱《解釋二》)出臺后,即使夫妻間有財產約定,離婚時房子也未必對半分。有人或許認為,把財產約定再去做個公證就能上雙重保險,鎖死房產歸屬。然而,新規賦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傳統公證文書的風險防范功能將受到極大挑戰,公證也并非萬全之策。
為什么公證突然失靈了?一是在于新規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開了綠燈。《解釋二》第五條明確規定,無論夫妻間房產給予約定是否完成不動產登記,在離婚訴訟中,法院都可根據婚姻關系存續時間、共同生活及子女撫養情況、離婚過錯、對家庭的貢獻大小以及房屋市場價格等因素,對房產歸屬及補償進行重新判定。也就是說,即便財產約定已公證甚至房屋已過戶,法院也有權依據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這讓夫妻財產約定公證的效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過去,憑借約定公證和變更登記往往能讓財產歸屬塵埃落定。如今,法院不再受其絕對約束。
二是在于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的法律性質進行了調整。與以往司法實踐不同,《解釋二》第五條采用的表述為“夫妻間給予房屋”而非“贈與房屋”,將夫妻間的房產更名或加名行為適用規則與普通贈與合同規則相區分。這一調整體現了夫妻間財產給予行為是以婚姻關系的建立和存續為基礎的,不能機械套用一般的市場交易規則。新規弱化了依據財產約定公證一刀切式的房屋分配,以綜合貢獻程度來匹配財產分配。
三在于公證模式本身的局限性。解釋二第五條強調 “給予目的” 的重要性,但夫妻間房產給予行為常摻雜復雜情感因素。如一方為了維系婚姻、換取對方忠誠而贈與房產,或一方以加名作為結婚條件等。公證機構雖會詢問給予目的,但難以完全探究當事人內心真實意思。一旦婚姻出現問題,當事人可能以“給予目的未實現”為由,要求重新分配房產,導致公證的效力在“給予目的”的考量下變得不穩定。
以往根據民法典658條,經過公證的贈與協議不可撤銷,在公證機構受理中,也不會特別考慮夫妻綜合貢獻程度。而新規出臺后,即使贈與協議經過公證,如果綜合考慮上述因素,財產約定中涉及的房產也有被重新分割的可能性。
舉個例子。小張和小李婚前達成約定,在雙方登記結婚后,小張要將名下房產過戶給小李,同時辦理了財產約定公證。小張婚后按照約定將房屋過戶給了小李,結果小李不久就提出離婚,小張要求小李返還房屋。
這種情況下,小張的過戶行為顯然是以建立、維持婚姻關系的長久穩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產居住價值為基礎的。在此前,處理這類情況沒有明確依據,現在依據《解釋二》第五條第二款可以認定房屋仍歸小張所有。因為雙方婚姻存續時間過短且小張無重大過錯,因此即便雙方的財產約定經過公證,也只能提升小李得到房屋補償的可能性,不能完全依據約定內容判決房屋歸屬小李。
綜上可知,即使經過公證的夫妻財產約定,也無法完全避免被撤銷的風險。即使房產已完成轉移登記,法院仍可根據婚姻關系的實際情況重新分割房產。
那么新規下,夫妻財產約定公證還有用嗎?蔡律師認為,公證并非就此被完全架空。公證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完全保證財產分配的結果,而在于審查當事人財產給予的真實意思,確保法律行為的公平性與合法性。現新規既然明確了財產分配的考察因素,公證機構可從該方向進行機制優化,在辦理公證時充分告知雙方的行為后果,固定雙方的意思表示,避免一方因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產繼而遭受損失。而普通人可以做的,則是在公證前對財產約定的具體條款進行調整,如明確給予目的是否以婚姻存續為前提、預設補償標準,婚姻解除時一方可收回房產等。具體應如何調整,我們后文再作詳細討論。
相關法規原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條??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
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銷的具有救災、扶貧、助殘等公益、道德義務性質的贈與合同,不適用前款規定。